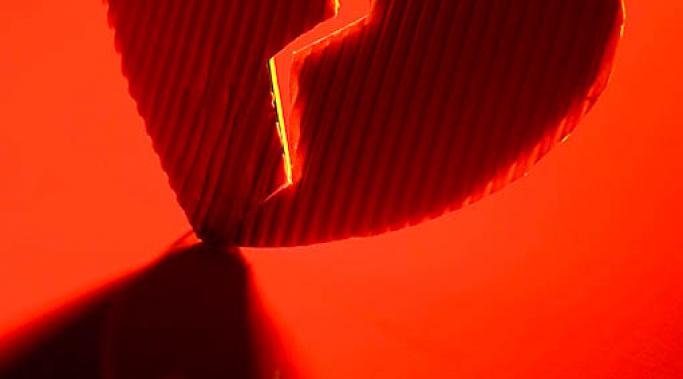上周,我写了我和一个受虐待的教堂的经历。说实话,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从我离开时发生的大规模遗弃中活下来的。但我知道,从宗教和精神虐待的痛苦中恢复是可能的。以下是一些治愈的步骤。
超过临界
Becky Oberg.
最近发布了一份新的纪录片,“为基督绑架”。虽然我除促销之外还没有看到任何东西,但电影造成了我的必看列表。这部电影是关于一个功能失调的基督徒行为修改学校和被非自愿发送的青少年。它带回了回忆。虽然我的父母愉快地从来没有把我送到多米尼加共和国,因为我的精神疾病,我担心他们会。有些孩子,包括一位我的高中朋友,并不幸运。然而,我以上帝的名义滥用,就像这些人一样,作为一种心理健康治疗的形式。
Becky Oberg.
有人说艺术有治疗作用。音乐也不例外。最近,我发现了三首歌,据我所知,它们不是关于边缘性人格障碍(BPD)的,而是出色地描述了它。这首歌是Meredith Brooks的Bitch, Billy Joel的She's Always a Woman to Me和Natalie Merchant的My Skin。
Becky Oberg.
当我在里士满州立医院时,我听说多个患者在不同的单位上,他们遇到了止痛药的困难。在Vicky的情况下,即使止痛药不是麻醉品,这也是如此。在Eric的情况下,当另一名医生止痛药时,员工非常愤怒。它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精神科患者有权患止痛药吗?”
Becky Oberg.
昨天,由于电力、暖气、屋顶和水的问题,我被从我的公寓撤离。我在收容所过了一夜,今天才回家。这不是一次有趣的经历,但它让我思考,如果遇到自然灾害,有精神疾病的人应该怎么做才能保持头脑清醒。
Becky Oberg.
精神疾病患者的权利是一个发展中的领域。有时法院的决定比我们做得更好——例如,法律规定,在危机中,只能用最宽松的手段来约束我们。然而,有时法院的决定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符合我们最大利益的并不总是法院裁定的正确。
Becky Oberg.
最近,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一家医院削减了精神病患者的病床数量,尽管事实上它已经以98%的容量运行。More Than Borderline的博客作者贝基·奥伯格(Becky Oberg)认为,精神病治疗虽然昂贵且无利可图,但不应该成为预算的牺牲品。
Becky Oberg.
老实说,我不具备所谓的“圣诞精神”。最近情况不太好。我被挑战去打架(当暴力伴随精神疾病时),我两岁的侄女做了手术,我的邻居去世了,我失去了一份工作。在一年中平常的时候,这是很多的打击,但在圣诞节前后…这让我明白了圣诞节并不总是每个人的欢乐时光。这是好的。
Becky Oberg.
在正常的一天,我可以走开。在这种精神疾病治疗设施中,我的邻居很少都是暴力的。也就是说,我的一个邻居有侵略史的邻居,最近开始用一系列B-Lords和F-Bombs挑战我,然后让我挑战一个拳击。我脱掉了我的眼镜,说我很好,只要她扔了第一个拳打。她告诉我“”$%!,你扔了第一个拳,我不是疯了!“一名社会工作者来了,摔倒了。我去了我的公寓并立即进行了哮喘发作(恐慌的物理疾病 -像症状)。我也打了一堵墙,瘀伤三个关节。不是我最好的时刻,而不是正常的。但后,我想到了精神疾病治疗设施暴力发生的事情时应该发生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