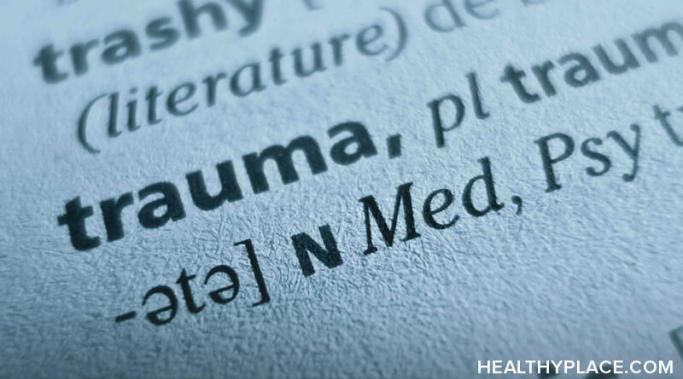我的名字是Juliana Sabatello,我很高兴地加入健康的地方作为“关系和精神疾病”博客的贡献者。我是28岁的佛罗里达州本土,我在迈阿密大学学习心理和人类和社会发展,我曾在佛罗里达大学的心理健康咨询。像许多人在心理健康领域一样,我变得兴趣,因为我在生活早期的心理健康的经历。自从幼儿早期以来,我患有恐惧,恐慌症,自11岁以来的第一个主要抑郁发作。精神疾病影响了我所拥有的每一段关系。
关于关系和精神疾病作者
米兰达卡
我加入了健美的地方,因为我开始估计我的慢性疾病的精神症状。多年来,我努力陷入困境,抑郁症作为我的类固醇的副作用,我的胃肠道麻烦发展的紊乱,以及来自健康问题的一生的创伤。但我从来没有能够将这些症状与我的物理相同。健康的局部社区帮助我验证了我与心理健康的斗争。但是,在慢性疾病的人中,Covid的时间对我们来说尤其如此可怕,我正在努力留在我的业务之外,我的研究生学习和健康。所以,虽然我会想念我的健康场地社区,但我决定留下这种关系和精神疾病博客,以减轻我的负荷并保护我的身心健康。
米兰达卡
许多慢性疾病患者发现自己有一定量的医疗创伤。当你是一个孩子时,在医院和生病的死亡中难以理解的手术,血液检查和时间。但是,如果我们的医生是更好的倾听者,我们也可以避免使用患有医疗创伤。
米兰达卡
如果不适用于我的每周虚拟治疗会议,我的避免依恋行为将导致我的检疫生命中的比例更加混乱。什么是避免附件?这不是精神障碍或疾病。相反,这是一个依恋的风格。
米兰达卡
当我第一次开始做爱时,我不知道我从事性观看 - 我没有意识到我正在分析并指导我在卧室里的行为,好像这是一种表现。但在某些时候,我意识到我的一个,唯一的专注于卧室,是让自己对那些演奏同行的男人有吸引力。
米兰达卡
性虐待后的性别:它是什么样的?性虐待对我的性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经过两次性虐待,我觉得我的性行为不再属于我。我的身体两次被视为我的虐待者所用的物体,因为他们看到适合,首先是在童年的家庭成员的手中,然后后来乘坐火车上的陌生人。虽然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我接受了我的性行为属于我睡觉而不是我的男人。我花了很长时间才面对性虐待对我性生活的影响的真相,我仍然没有解构这些滥用情况的许多方式,最终将我带到了我现在的性别的经历。我决定将这个博客用作探索这一点的地方。
米兰达卡
我的名字是Miranda Card,我很高兴加入健康的球队作为“关系和精神疾病”的作家。许多我对精神疾病的经历源于终身与慢性疾病的终身斗争,一种称为Behcet的疾病。只有现在,在24岁时,我开始了解我的诊断的创伤。我现在只开始承认,我的病情超出了身体的症状;它已经蹂躏了我与食物和出生紊乱的饮食的关系;它激发了影响我在生活中的决定的焦虑;随着我的药物治疗的抑郁症经常对我的关系造成严重破坏。以书面形式讨论这些东西从未发生过,因为这些“精神症状”一直是羞耻和否认的源泉。但是有人最近告诉我,写下你害怕的是什么,所以在这里我是。
汉娜·奥格雷迪
我的名字是Hannah O'Grady,我很欣喜若狂,说我是在健美的健康场所的关系和精神疾病的新作者。心理健康在我的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个人和专业的情况下。我渴望为我的读者的写作,关系和心理健康相结合,我期待着与阅读本网站的人。
乔纳森伯格
我的名字是Jonathan Berg,我很高兴能够与你分享我的故事,并加入健康的人的关系和精神疾病团队。当我14岁时,我被诊断出患有双相障碍II型。从一开始,我把它从大家里藏起来,包括我最亲密的朋友和父母。我害怕人们会认为我很疯狂。我很伤心地说,这种担心持续了超过20年。